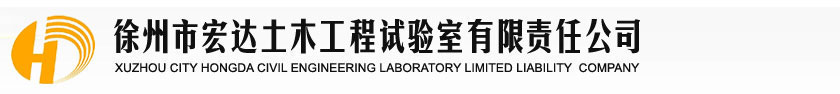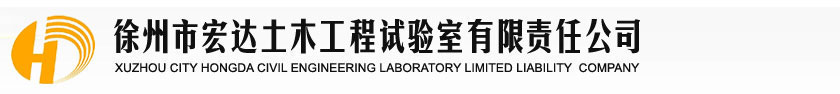在小的时候,我最怕干农活了,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里,捆着麦秸,麦芒很是扎人。
“我也知道扎人啊,吃得时候,从来没有听你说啥。”父亲他老人家也会说我几句,当时刚进入青春期的我听着父亲的话,心里还是不舒服的,“咋这样呢,一点面子都不给留。”心里总是这样想着。
“爸,麦芒不扎你吗?真得一点都不痛?”我问道。
“痛啊,我也热啊,一想起来一大家子都要吃饭,就不痛了。你读书上课,是不是也累吧,看你天天也去学校,也没有看你说累。”父亲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,又与我的学习联系在了一起。
我还能说啥呢,惟有低头去干活,就那样,一句不吭地、默默地跟随着父亲。虽然心里多少还有点怨气,但一想“父亲都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已在田间里劳作”的镜头时,心里也有了些释然。
故乡丰县,是一望无际的平原。故乡的麦田极有特色,从弱不禁风的麦苗到绿郁郁的碧波再到金黄色的麦浪。我们那里土壤的土质很好,沙土地,这与黄河决堤有着很大的关系。在全国来说,能说得上的东西有不少,比如,甜中夹带微酸的丰县红富士苹果、大大个头的脆梨、访亲必备的峰糕、享誉海内外的泥池美酒......在小时候,我们庄里和庄外都是泥土路,每年到了夏天,泥土飞扬啊,我在路上飞奔时,身后都扬起尘土,好开心啊,浑身都是土,跑到西河(大沙河),一个猛子下去,啥都解决了,干干净净的。但是,当跑到家时,浑身又是一身土。也许那就是生活,那就是少年吧。
父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庄稼人,他在那一小块田地里,种出了生活的气息。地里有莴苣、有豆角、有茄子、有黄瓜、有麦子、有玉米、还有豆子......父亲持家的能力绝对是一个高手,我们家的餐桌上总是有各种蔬菜,母亲也想尽办法让菜更有家的味道。
我凭着记忆,能够说出来一些与麦子相关的工具:锄头、犁子、耙、铁锹、镰刀、木掀、耧车......但那时就已是机械播种和收割了,镰刀只能用来割一割联合收割机割不到的田埂或地头的麦子。
记得那些年,每到傍晚,天气有点凉了,翻出的泥土味就很好闻,有一种独特的馥郁芳香。父亲对于犁地和耙地有着自己的见解,他说道:“一块地,如果没有经过犁地和耙地,是不会长出好庄稼的,以往都是人工犁地耙地,现在有了拖拉机,倒是省事了。”犁地一般在春秋两季,到了初秋季节,就是拖拉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,犁地即耕田,是用拖拉机将田地土壤翻动,便于耕种。耙地是在犁地之后进行的一种表土耕作,通常在犁耕后、播种前或早春保墒时进行。
丰县的小麦都是秋播的。当然,在全国因气候有着差异,也有春耕和春季小麦的。
秋收时,我们就已经把玉米、豆子等都收到家里了,接下来,就要夜以继日地开始忙秋耕。太阳温度高,晒着大地,泥土被晒得烫人,踩在地上,双脚都疼得不得了,好像只有这样,来年的农作物才能长得好。每年的秋天,大约是9月下旬和10月上旬,就会把麦种播种在地里,这就是冬小麦。晒好的土壤再加上犁地时撒入的人工粪肥或有机化肥,初秋的土地就成了麦种温馨而肥沃的产床。坐在地头或田埂上,看着拖拉机犁地和耙地的场景,真是一种行云流水般的享受。
到了来年6月中旬就要开始收割小麦了。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,经历了太多太多了,从整地、施肥、播种、除草、浇水……那么多个日日夜夜。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庄稼人,深知“汗滴禾下土”,“粒粒皆辛苦”的内涵。望着在泥土中滑行的镶嵌在拖拉机尾部的犁铧,它是那么锃亮,在秋光的照射下,闪着白光,与风声和笑声交织成了一幅画卷。肥沃的土地在犁铧的前行中打着滚,躺成一行一行,庄稼人的期望眼神融进泥土中,与夕阳相伴,撒下对来年丰收的祝福。
白居易曾感叹道:“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”冬季过去,在春天里,麦子便整整齐齐。春风过处,是扑鼻的清香。在不知不觉间,麦苗长成了麦秸,墨绿变成了金黄。这是时光的洗礼,也是对于硕果和成熟的迎接。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土地最懂得知恩图报,种子也是,只要双脚不离开田地,只要双手紧握锄头和铁锹,只管耕耘之心不变,季节一定会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。
“小麦深如人,澶漫不见地。”6月份,又到了麦子金黄的季节,上周末,我回了一趟老家,望着翻滚的麦浪,闻着醉人的麦香,抚摸着沉甸甸的麦穗,金灿灿的黄色铺满了整个大地。大沙河啊,家乡的母亲河,守着这片金黄色的原野,讴歌着对于未来的憧憬...
|